提起鴉片戰争,但凡接受過基礎教育的國人都不會感到陌生(shēng),毫無疑問,這是近代滿目瘡痍的開(kāi)端。然而對于絕大(dà)多數人來說,鴉片戰争僅僅意味着曆史教科書(shū)中(zhōng)一(yī)段冰冷的文字,幾個在戰争和外(wài)交場合做出愚蠢決定的大(dà)臣,以及戰争結束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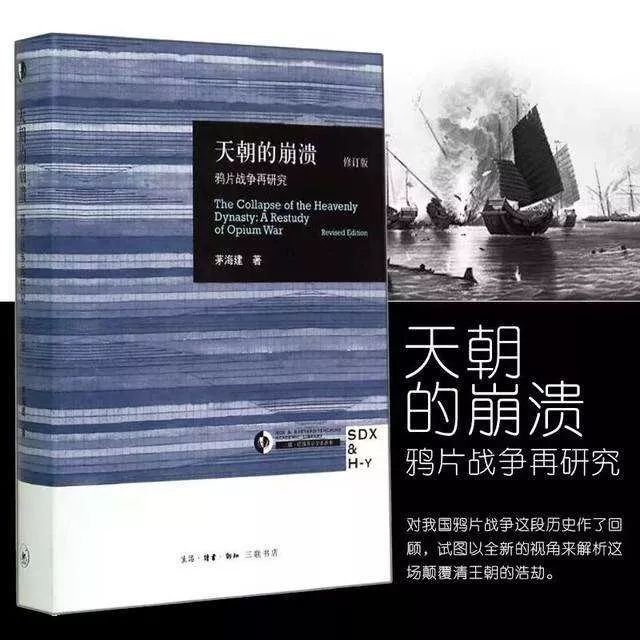
圖片來源網絡
或許曆史老師在講述這段距離(lí)我(wǒ)(wǒ)們已有将近兩個世紀的曆史時,會用到“腐朽、沒落、愚昧、無能”這些字眼,這種站在上帝視角的批判看似是對過往的反思,但卻沒有任何貼近曆史的溫度,僅僅是将整個民族所經受的失敗、屈辱全部歸罪軍事将領與外(wài)交大(dà)臣,以一(yī)百多年後的觀念去(qù)推測古人。
茅海建先生(shēng)于1994年所著的《天朝的崩潰——鴉片戰争再研究》以全新的視角對鴉片戰争進行了理性分(fēn)析,通過對清朝的軍事力量、戰争過程、條約的簽訂等一(yī)系列史料的研究,試圖以當時的道德觀念、思維方式與行為規範去(qù)理解曆史。茅先生(shēng)在自序中(zhōng)談及:“盡管現代史學理論已經證明了再現曆史之絕對不可能,但求真畢竟是治史者不滅的夢境。”絕對的複原曆史是不可能的,但曆史研究的意義正在于通過不斷地推論,更加貼近曆史事實,從而獲得真正的曆史經驗,以規避災難的重演。

圖片來源網絡
傳統中(zhōng)國史與事實之間的差距
打開(kāi)中(zhōng)國傳統史籍,人們往往會看到對于善惡忠奸的評判,這種基于道德的判斷是最容易做出的,隻要曆史人物(wù)的觀念或做法合乎後來人的價值判斷,就會被定義為“善”,反之亦然。很少有人去(qù)關心事實真相,人們總是會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方面。
在鴉片戰争中(zhōng),善的一(yī)方往往被定義為嚴禁鴉片的林則徐、虎門大(dà)戰中(zhōng)戰死的關天培、三元裡抗英中(zhōng)英勇作戰的廣東民衆,惡的一(yī)方則被定義為“賣國”的琦善、戰敗的奕山、簽訂《南(nán)京條約》的耆英。茅先生(shēng)卻在緒論中(zhōng)大(dà)膽地否定了琦善的“賣國”罪名,琦善被控的罪名主要有四條:主張弛禁鴉片、打擊禁煙領袖林則徐、虎門危急時拒不支援導緻戰事失敗、私自割讓香港予英國。然而在對當時的史料詳細分(fēn)析之下(xià),這四項罪名竟無一(yī)成立。
中(zhōng)國人向來稱贊“玉碎”的品格,認為在兩國對抗中(zhōng),隻有強硬的态度才是“忠勇”的體(tǐ)現。這種看法雖然在道德層面上容易獲得民族情感的認同,但僅僅強調精神而忽略現實顯然是不客觀的。
戰争最基本的實質是兩支軍事力量之間的對抗,在茅先生(shēng)的分(fēn)析之下(xià),我(wǒ)(wǒ)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:
1、從武器裝備上來看,“英軍已處于初步發展的火(huǒ)器時代,而清軍仍處于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;
2、雖然清朝在鴉片戰争中(zhōng)處于兵力上的優勢,但清軍的性質更傾向于維護地方治安的警察,布防極為分(fēn)散,沒有一(yī)支可集中(zhōng)力量用于作戰的軍隊;
3、官兵的選拔方式更傾向于傳統的冷兵器作戰,而并不适用于近代化的軍事作戰。
因此,無論從民族情感上多麼不願承認,在一(yī)支近代化軍事力量的降維打擊之下(xià),鴉片戰争是一(yī)場注定會失敗的戰争,大(dà)臣的善惡忠奸在曆史事實中(zhōng)産生(shēng)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。将戰争失敗的結果歸罪于不主張強硬對抗的大(dà)臣,而疏于對國家組織形式的反思,這是一(yī)種最易獲得的結論,也是一(yī)種最無意義的結論。

圖片來源網絡
流血與迷夢
鴉片戰争毫無疑問是一(yī)場流血且失敗的戰争。雖然當時的清政府已經百病纏身,孱弱不堪,但它仍然以“天朝上國”自诩,在戰争之前,沒有任何一(yī)個人相信天朝會不敵區區“島夷”。因此,這場武力抵抗與戰争中(zhōng)的流血犧牲是不可避免的,之後的議和則是一(yī)個弱國在戰敗後所做出的無可奈何的利益讓步。
茅先生(shēng)認為“以鮮血而赢得勝利,自是其價值的充分(fēn)體(tǐ)現。以鮮血而換來失敗,也可能不是無謂的,即所謂‘血的教訓’。一(yī)個失敗的民族在戰後認真思過,幡然變計,是對殉國者最大(dà)的尊崇、最好的紀念。清軍将士流淌的鮮血,價值
然而,鴉片戰争所流淌的鮮血并沒有體(tǐ)現其價值:“盡管戰争的結局是殘酷的,但道光帝并沒有作深刻的自我(wǒ)(wǒ)反省,仍是一(yī)如既往地将一(yī)切責任卸于下(xià)屬。牛鑒逮問後,他又(yòu)将奕山、奕經、文蔚等前敵主将送上刑部大(dà)堂,統統定為斬監候。他在内心中(zhōng)認定,戰敗的原因在于這批奴才未能實心實力辦事,‘天朝’的厄運在于缺乏忠賢智良之臣。”在這種舊(jiù)有的思維方式與體(tǐ)制之下(xià),沒有任何一(yī)個經曆鴉片戰争者對制度産生(shēng)疑問,甚至被捧上神壇的林則徐在病中(zhōng)口授的遺折仍然是臣子對于君主的一(yī)片忠誠,而并無對改變時局的思考。
付出了如此慘痛的代價,沒有人從“天朝上國”的迷夢中(zhōng)蘇醒,人們簡單地評判完善惡,便将這次戰争抛諸腦後:“議和之後,都門仍複恬嬉,大(dà)有雨過忘雷之意。海疆之事,轉喉觸諱,絕口不提,即茶坊酒肆之中(zhōng),亦大(dà)書(shū)‘免談時事’四字,俨有詩書(shū)偶語之禁。”
正是這種傳統的歸罪于人的思維方式,使我(wǒ)(wǒ)們忽略了整個國家所存在的問題,反而形成了一(yī)種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,認為隻要重用賢臣就能反敗為勝,從而導緻了十幾年後第二次鴉片戰争的慘敗與火(huǒ)燒圓明園的屈辱。
曆史的教訓與現實的思考
步入21世紀已有将近二十年之久,中(zhōng)國的硬實力與軟實力毫無疑問得到了極大(dà)的提升,而實現中(zhōng)華民族的偉大(dà)複興對我(wǒ)(wǒ)們來說仍然是一(yī)項艱巨的任務與挑戰。
當我(wǒ)(wǒ)們回憶起這段落後于人的曆史時,總有人認為這是當政者與戰敗者的責任,但我(wǒ)(wǒ)們往往忽略了一(yī)件事:能夠站在上帝視角評判的永遠是後來者,沒有任何人能不被自己所處時代的局限性所影響。盡管鴉片戰争距離(lí)我(wǒ)(wǒ)們已有将近兩百年之久,但傳統“明辨善惡忠奸”的固有思維對我(wǒ)(wǒ)們的影響無疑是可怕的,似乎隻要有人被推出來承擔責任,我(wǒ)(wǒ)們就可以忽略體(tǐ)制本身所存在的問題。
作為中(zhōng)國近代的開(kāi)端,鴉片戰争是讓中(zhōng)國人感到屈辱和痛心疾首的。如今,鴉片戰争已然遠去(qù),現代化的進程還在不斷推進。以往的經驗證明,單純的失敗并不能成為成功之母,隻有正視失敗、認真總結、不斷革新者,才有資(zī)格讓失敗成為成功之母。一(yī)段失敗的曆史,其意義正在于——不讓曆史重演。